收视率吊打《繁花》,这才是国产真神剧
来源:独立鱼电影 人气:22285 更新:2024-01-06 15:22:53
近期最火的国剧,莫过于《繁花》。
王家卫「下凡」拍电视剧,腔势很浓。
一道简简单单的排骨年糕,也成为了上海滩意难平。


很多人喜欢,直夸拍出了「老上海味道」。
也有人不喜欢,觉得太过花里胡哨,徒有其表。
还有相当一部分原著党,表示甚是遗憾。
毕竟,原著中许多的重要情节,都没有拍出来。
特殊时期剧情的删减,也让宝总的人物厚度大打折扣。

种种讨论,鱼叔不由得想起一部30年前的老剧。
片中故事的年代,正巧与《繁花》一样
不论是尺度还是味道,都是我心中,最牛X的沪剧——
《孽债》


当年《孽债》的火爆,是现象级的。
在沪语地区创下了42.62%的平均收视率纪录,说是万人空巷也不为过。
但首播之后,《孽债》沪语版遭到雪藏,直到2005年才借十周年重播。
其中缘由,或有「推普」大环境下对各地方言剧的限制。
又或许,是其中敏感的时代背景。

时隔30年再看,仍会惊讶于其「敢拍」。
本剧改编自作家叶辛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波及上千万人的一笔孽债。
50年代,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席卷全国。
城市中的年轻人下乡插队,在那里挥洒青春,扎根生活。
到了70年代末,随着形势的变动,又掀起了「知青大返城」。
但由于政策规定,他们在农村的伴侣和孩子,无法一同回城。

十几年后,当年被滞留的孩子们长大了。
出于对身世的好奇,他们结伴前往大城市寻亲。
本剧的剧情,便由此展开。
五个半大的孩子,攀上从西双版纳到上海的火车。
一路上神采奕奕,期待着见到自己的「阿爸」「阿妈」。

从天而降的亲骨肉,却让父母们措手不及。
他们大多隐瞒了插队的过往,也组建了新的家庭。
如何安顿孩子,又如何处理新家庭的矛盾,变得尤为棘手。
「就像朝各自家的窗户里扔进一颗炸弹」

半大孩子愣生生闯入重组家庭,引发一系列动荡。
每一条支线剧情,同样不乏禁忌的情节。
比如,姐弟乱伦。
天华与玉敏的情感线,相信是不少人的情欲启蒙。
异父异母的姐弟俩,逐渐擦出了火花。


再比如,未成年犯罪。
孩子们带着云南边境的野生感,一头扎进了上海这座现代化城市。
为了搞钱,他们生出了不少鬼点子。
或是带来了家乡特制的香烟,掺入大麻、罂粟来吸食、贩卖。
或是仗着拳脚出众,带女孩玩起了「仙人跳」。
诸如此类,单拎出任意一项,都不可能在今日的国产剧中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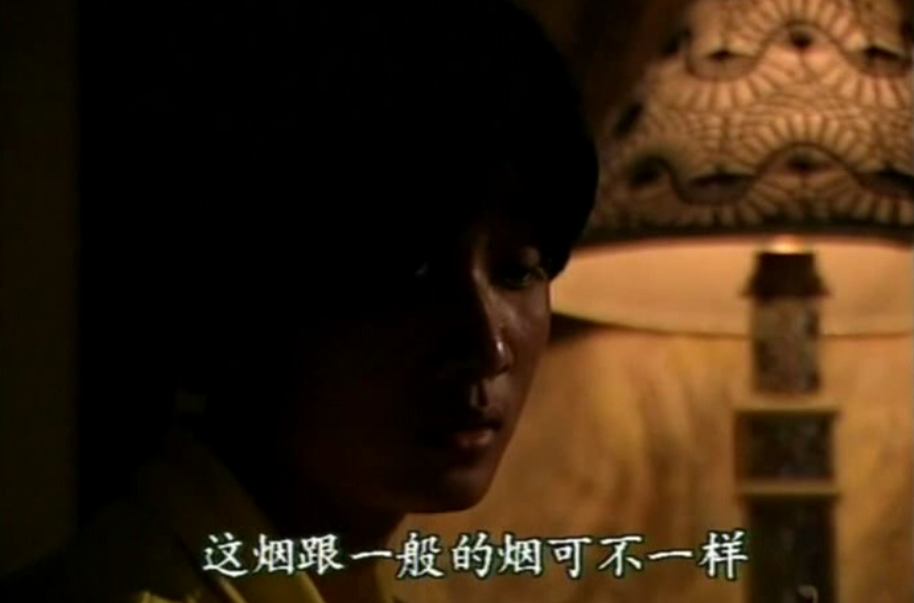
台词上,也往往直戳系统要害。
外地孩子生了病,住院开销甚大,医保却不予报销。
角色对户籍、医保制度的质疑,也道出了普罗大众最关心的话题。

还有对血亲与婚姻的怀疑。
从一段错误的过往,审视现当下的种种现象。
通过几个知青的内心斗争,冲击着婚姻制度的框架。

这些生猛的设计,最终又落回几个寻亲的孩子身上。
身世浮沉雨打萍,就像片尾曲里唱的那样:
「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
「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
「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


所有的「敢拍」,都建立在「会拍」的基础上。
否则便会滑入刻奇,乃至消费苦难。
导演黄蜀芹,是中国第四代导演领军人物。
无论是的电影《人·鬼·情》,还是电视剧《围城》等作品中,她都贯彻「拍好每一个人」的理念。

《孽债》中,五个孩子对应着五对父母。
如此多的人物,要在短短20集中刻画到位,难度可想而知。
黄蜀芹却游刃有余,有时只需几句台词,就能精准定位人物。
五个孩子里,永辉是最失落的一个。
别的小伙伴都住进了父母家中,他却被安排进了招待所。
父亲当上了有钱有权的经理,一句质问令永辉瞬间委屈得两眼含泪:
「你有什么证据」

当年,父母为了回上海,将永辉卖给了一对农民夫妇。
说好了假离婚,可父亲一回到上海却当起了「陈世美」。
借丈人家的关系,在外贸公司做得风生水起。
如今正值晋升的当口,他绝不想因为永辉搞黄了事业。

导演没有花费过多的笔墨。
又用一句台词,精准点中了夫妻俩的特性。
「时间就是钞票」

最纠结的一个,是思凡。
爸爸和后妈都是普通职工,待人宽厚善良。
但问题是,家中房子实在太小。

豆腐干大的亭子间,生生塞进一个半大小伙。
一家人的生活承担着巨大的不便,就连夜里用痰盂都很不方便。
后妈的耐心与包容,也在一天天被消耗。

最让人心疼的,则是美霞。
她是所有孩子中年纪最小的,也是最惹人怜爱的。
妈妈离世后,她在云南孤苦伶仃。
不远千里带来的药材,寄托着母女俩对爸爸的思念。
「当归就是应当归来」

她的爸爸沈若尘,是观众们心目中的好爸爸。
他对美霞的爱与愧疚,是肉眼可见的。
多年来,他始终放不下云南的妻女。
因此,他格外珍惜这次父女团聚的机会,将其视为一个还债的机会。

但,纵然有了决心,现实仍有重重阻碍。
妻子这一关,很难做思想工作。
当年沈若尘欺瞒了自己的过去,令他失去了商讨的底气。
强求妻子的接纳,又是另一种不公平。

即使妻子硬着头皮答应。
小儿子这一关,又一时难以适应。
娇宠惯了的独生子,对美霞龇牙咧嘴。
动辄大骂「乡巴佬」,还摔碗筷、拿球砸她。

街坊邻居的指指点点、风言风语,同样难以忍受。
几个孩子的境况各有不同,却都到了呆不下去的地步。
一个大雨夜,他们计划逃离上海。

《孽债》刚播出时,也曾受到不少的批评。
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字,卖惨。
但,细细看来,不止有悲惨。
通过回忆闪回,还原每个人身上这段孽债的来龙去脉。
在思凡的爸爸身上,看到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当年他下定决心回到上海,立志要做一番事业。

可是,十余年过后,他只是做着电影放映员。
单位不给分房,连安顿亲生儿子的地方都没有。

在天华的阿妈身上,可以看到不同环境下相同的女性困境。
云南的前夫好逸恶劳,还出轨成性。
她不堪屈辱,才忍痛将儿子留下,独自逃回了上海。
「你要离婚,休想」

可回到上海,又落入了同样的局面。
儿子的突然到访,也成了丈夫要挟的条件。
她被迫忍受丈夫的吃喝嫖赌。

在沈若尘身上,还留着一点文人骨气。
当整个时代都疯了,他仍然想要追问。
他想要的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幸福,却造下了悔恨一辈子的孽。
「人人都能回来,为什么我不能回来?」

剧情的结尾,几家欢喜几家愁。
孩子们大多要回到故乡。
从上海开往西双版纳的列车起步,像极了当年父母启程那般。
五个孩子,只是偌大时代的小小缩影。
「这样的故事并没有完,这样的故事也许还有很多很多」


剧中,沈若尘曾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
他几乎咆哮着,点明了全剧的主旨。
这个孽,不是一个人作的。

一句话,说起来很容易。
我们可以轻易地归因于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那段不可细说的往事。
但,黄蜀芹导演却选择具体、直观地面对。
在塑造鲜活人物之外,她利用大量闲笔勾勒了上海这座城市。
美霞曾与爸爸有过一段对话。
之所以来上海,不仅是寻亲投靠,也是想解答一个困扰母女俩多年的疑问:
这座城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可以让人抛弃血亲骨肉。

与《繁花》一样,《孽债》将故事设置在90年代初期的上海。
但,后者没有滥用特写,也没有利用前景来打造所谓的上海腔调。
毫不避讳的全景镜头,不时扫过光秃秃的外滩,与即将竣工的东方明珠塔。
这些大场面,收录了彼时上海的社会风貌,使《孽债》成为了一部重要的城市影像资料。

弄堂中,居民住房被分成了亭子间、棚户区。
陡峭且狭窄的楼梯,承载着小市民们每日的奔波。

靠近郊区的地方,新建了高级公寓、花园洋房。
做产业的家庭,过上了更惬意的小资生活。

早茶馆子里,鱼龙混杂。
左边一桌子,衣着休闲且有说有笑。
不用说,想必是公款吃喝的公务员。

右边一桌子,坐着西装笔挺的老克勒。
手边一前一后摆着香烟打火机,左顾右盼着。
是个烟贩子,准没跑了。
摆法一变,又成了赌钱的暗号。

五个孩子的家长,也分别代表着当时不同的社会阶层。
报社编辑、外贸经理、普通职工,还有混江湖的暴发户。
财富、地位、资源的不同,让他们应对问题的方式迥然不同。
同样也寓意着:他们的遭遇,是覆盖了整个社会的。

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
炒股票、接私活,猪站在风口都能飞起来。
「在上海滩上有钞票就是爷」

每个人都在向「钱」看,不失为另一种「大跃进」。
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与人之间谈何相互理解。
工厂内,职工们对那帮知青无比唾弃。
「他们这种人真是前世作孽,还结什么婚呢」

可同时呢,产业升级也造成了大面积的下岗潮。
外贸做得越漂亮,领导面子上越风光。
转型不及时的工厂,说淘汰就淘汰了。
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小老百姓。
当时代的尘埃落在自己头上,才会发出抗议与呼救。

再回过头来追问,这笔孽债该怎么算?
恐怕仍然找不到答案。
但,即便是无解,也不能否定追问的意义。
《孽债》所做的,是从人的视角看见城市,再从茫茫城市中找到人。
城市是冰冷的,有人才有了温度。
「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

热门资讯
- 悲痛!网红“涛哥”去世,死因曝光获百辆豪车送殡,赵本...
- 善恶终有报,这一次张译的话终于应验了,将“众星”底裤...
- 景甜新浪大楼亮相,圆脸大眼睛“富贵花十足”,生图也白...
- 无知还是有意为之?霍尊直播唱禁歌!
- “偶练”毕雯珺、“创1”李子璇,那些错过成团的练习生还好...
- 王俊凯,刘雨昕,王鹤棣,王子异,任泉
- 68岁张国立疑定居法国!紧抱娇妻现身高档餐厅,生活质...
- 《奔跑吧9》再次迎来家属助阵,郑恺老婆加盟,全员整蛊...
- 张雨绮:这个情路悲苦的女人,终于“解脱”了
- 王思聪又结新欢?与才17岁的姚心怡去米其林,一身穿搭...
- 曾志伟重返TVB连升三级,荣升行政委员会成员,与高层同...
- 何炅谢娜再合体乘风姐姐与好6团合跳《你好,星期六》主...
- 《法证先锋5》宣传活动买粉丝造势?TVB:不是事实
- Angelebaby翻译成中文是什么?Baby在跑男上就已给出了...
- 无视节目组规则,《极挑》后期人员这一手操作,在打导...
- 中国好声音:两轮战队赛之后,哪些学员有望成为总决赛...
- 也评电影《满江红》:解锁“九连环”般故事背后的家国情怀
- 18年后再看袁茵,才看懂她当年为何会离开侯耀文,转身...
- 王俊凯与天王同台,粉丝:这是要开启宇宙级演唱会吗?
- 又一部生猛韩片诞生,被打出9.5分,轻松夺下票房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