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中“内卷化”的表现,带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来源:赵有娱 人气:24112 更新:2022-11-25 20:56:15

“内卷化”的另一表现是对社会现实阐释的自我重复,表现在娄烨等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中长达三十年对底层社会的书写。
娄烨电影在叙事内容上注重完整性,电影的叙事内容表达得越细致,观众需要思考的内容就会减少,需要挖掘的影像中的含义也就随之减少。

一旦影像阐释的内容变得细致入微,观众接收到的信息就会变多。那么无论是拍摄技巧、影像表达上的深层含义和文化表征都会随之减弱。
大多数研究者将娄烨电影的特征归纳为它们致力于描绘异质性的底层社会景观、边缘化人物群体,无论是《苏州河》中河两边的底层人民生活还是《推拿》中的盲人群体。

它们也代表着第六代导演在电影界被边缘化的身份,而当他们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却在影像的表达上少了自我的表达,开始从社会中选取类型化的人物。此时,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的选取的拆迁办主任和暴发户,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人物。
从指代自我到指代生活在边缘社会的他者,人物群像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从《周末情人》、《危情少女》等早期电影中的都市群像是身体狂欢,到《颐和园》中余虹开始具有宏大的象征意味,是从身体狂欢到生命狂欢的过渡,直到《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电影中从林慧的身体狂欢和生命狂欢的失衡中,寻求精神狂欢。
电影开头用拆迁户的不满和喧闹,展现城中村中普通个体的群像,正如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中《我不是药神》中的多次群像化场面一样。

电影中人物的变化是《周末情人》中李欣、《苏州河》中的马达、《颐和园》中的余虹等那些在行动、思想和情感上丰富的圆形人物,到《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角色设置的扁平化,这些都是社会化了的人物,他们是被置于故事背景之下的,被嵌入在了史诗般的时间和复杂的社会问题之中。
那些在青春期的个体欲望逐渐上升为社会欲望。除去影像表达和人物的变化,空间的意义生产也逐渐缩减。

目前关于内卷化,有更为朴素的解释,形容竞争的激烈程度的增长,也有人称之为非理性的竞争,当所有电影导演或者某一导演投入更多的精力在相同的类型上时,会造成整个产业的停滞不前,这也意味着有效的创新,意义生产上充满更多内涵和变化,娄烨导演如何迈向“去内卷化”也变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可以看作对下一部作品的期待。
电影本身是不能够脱离整个大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的,所有电影无论是以怎样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出现,最终都是表达的现在人对历史故事的看法,借古喻今。电影本身总是会直接地与社会发生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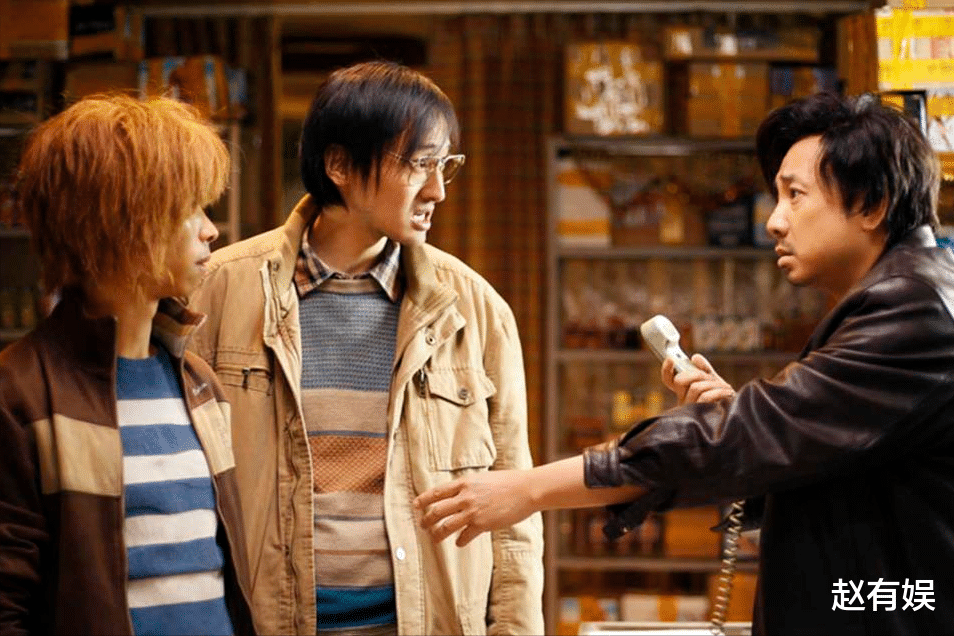
如今艺术作品的创作是相对自由的,是艺术家释放才华和观点的平台,使得电影人能将更多历史的真相放进去,从生活空间中躲开被权力操控的那一部分。文化的更加多元性,也使得方言、地域性文化特征被充分运用在电影创作中。
2007年国内电影市场才开始逐渐走向商业化,而此时娄烨的电影作品还处于地下状态,从诸多研究中将娄烨的电影划分在独立电影之列,电影面临了很多困境。审查制度的增强以及电影市场的逐渐繁荣,既是限制了艺术电影的发展,又是增加了电影的竞争力。

如今现象级电影频频产生,票房不断飙升,电影受制于市场、资本和受众,艺术电影如何与主流的商业电影竞争,如何在艺术性和现实性达到一种平衡。
抱着对电影的事业的热爱和电影人本身的责任感,2012年开始,娄烨的电影开始逐渐转向地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耗时两年,才登上荧屏,离不开娄烨的自我审查和在保留艺术性的同时不断删减镜头,是对电影商业性的一种妥协,也是为了急切的向观众传达《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暗藏的精神内核和人性思考,以及对历史的一种看法。

娄烨导演创作的电影也逐渐开始商业化和类型化。国内电影市场的不断繁荣,也让第六代导演开始迎合受众的需求。如今,处于代际更替的动态过程中,第六代导演成为了主流的稳定的创作群体。
那就意味着关于空间造型、空间叙事、空间生产的诸多方面的表达上,形成了固定模式的同时,内卷化现象造成娄烨电影中对空间造型上的细致和叙事功能的改变和都市空间转向带来的社会主体身份的变化等引起其空间意义的下降,使得娄烨的电影空间随着第六代群体的变化和新时期的影响下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一方面是与第五代导演构成的空间造型和社会空间的决裂,另一方面是在新题材内容上的自我重复。
娄烨等导演的成熟期是随着电影产业的逐步发展的外部条件下,因此,商业因素也成为了一种转变的因素,边缘到主流必先要经过商业力量的推动,在整个电影创作过程中要迎合大众审美的时候,必然会失去一些个人化表达、先锋性。
热门资讯
- 悲痛!网红“涛哥”去世,死因曝光获百辆豪车送殡,赵本...
- 善恶终有报,这一次张译的话终于应验了,将“众星”底裤...
- 景甜新浪大楼亮相,圆脸大眼睛“富贵花十足”,生图也白...
- 无知还是有意为之?霍尊直播唱禁歌!
- “偶练”毕雯珺、“创1”李子璇,那些错过成团的练习生还好...
- 王俊凯,刘雨昕,王鹤棣,王子异,任泉
- 68岁张国立疑定居法国!紧抱娇妻现身高档餐厅,生活质...
- 《奔跑吧9》再次迎来家属助阵,郑恺老婆加盟,全员整蛊...
- 张雨绮:这个情路悲苦的女人,终于“解脱”了
- 王思聪又结新欢?与才17岁的姚心怡去米其林,一身穿搭...
- 曾志伟重返TVB连升三级,荣升行政委员会成员,与高层同...
- 何炅谢娜再合体乘风姐姐与好6团合跳《你好,星期六》主...
- 《法证先锋5》宣传活动买粉丝造势?TVB:不是事实
- Angelebaby翻译成中文是什么?Baby在跑男上就已给出了...
- 无视节目组规则,《极挑》后期人员这一手操作,在打导...
- 中国好声音:两轮战队赛之后,哪些学员有望成为总决赛...
- 也评电影《满江红》:解锁“九连环”般故事背后的家国情怀
- 18年后再看袁茵,才看懂她当年为何会离开侯耀文,转身...
- 王俊凯与天王同台,粉丝:这是要开启宇宙级演唱会吗?
- 又一部生猛韩片诞生,被打出9.5分,轻松夺下票房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