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设悬角度看,其在反转电影中扮演什么角色?
来源:娱之萌宠 人气:35644 更新:2022-07-08 20:56:49

西方小说理论家戴维·洛奇说:“小说就是讲故事,讲故事无论用什么手段,总是通过提出问题、延缓提供答案来吸引住观众的兴趣。”
而反转叙事相较于直叙、倒叙、插叙等表现手法,恰是通过对于悬念的设计来误导观众,在人物、情节、时空等元素的反转下,在释悬处颠覆观众的认知,从而带给观众始料未及的情感体验,其在影片的逻辑架构和叙事策略上更具挑战性。

由此,通过设悬-逆转-释悬的逻辑结构,对于反转叙事的策略进行分析和梳理。
不过要明确的是,虽存在并未完全按照上述逻辑进行的反转叙事,如先抛出谜底再进行释悬或将释悬部分省略的叙事行为,但“反转”想要达到惊奇的效果必然离不开上述三个叙事环节。
基于此,我将从设悬角度去看反转的叙事策略,其在反转电影中扮演什么角色?并对此进行深入地分析。

反转叙事得以运行的前提在于悬念的设置和铺陈,而叙事上的空白与延宕正是制造悬念的惯用技巧。
伊瑟尔在《阅读行为》中提出了存在着一种“意义空白与未定性”即“召唤结构”。他认为“未定性”包括两种结构样式:空白和否定。空白是指文学的文本中并没有明确写出的事情,是文本结构中的叙事断裂,它会触发受众进行想象活动,同时获得新的视野。

在反转叙事的电影中,创作者通过信息的压制形成叙事断点,从而“召唤”受众对于空白的填充和解读,后通过新的信息的进入与之前的读者想象形成反差,从而在不断地猜测与解谜的过程中形成反转,以此来获得新的世界模型。
电影叙事是一种阐述序列,观众通过对叙事时间上因果链条的情节输出,从而对电影事件进行认知性的解读和意义的生成,但叙事断点的运用,是为了遮蔽事件全貌,在反转到来前形成铺垫,使观众在残缺不全的信息中产生悬念。

卡法勒诺斯指出“故事中发生断点的两种可能模式:叙事要素的暂时缺失或永久性缺失”,二者指向的都是观众知悉的信息少于人物。在影片中,叙事元素的暂时缺失表现为信息的延宕,是在叙事过程中省略了一些细节和情节解释,待高潮或结尾再进行展开。
如电影《你好,李焕英》观众跟随贾晓玲的视角一起穿越回了母亲年轻的时候,在和母亲一起买电视机、比赛、相处的过程中,将贾晓玲母亲也穿越回去的信息进行延宕,到影片结尾处才予以展现,使受众获得了母爱与个人“救赎”的情感体验与戏剧化、惊奇化的叙事满足。

叙事要素的永久性缺失则被称为信息的压制,多以开放性的结局收场。虽然同样无从知晓创作者有意遗漏、省略的信息,但创作者只将所谓的“结局”提前告知给观众但不予解密,以此来积渐悬念让观众进入想象性视域中自行解读,从而形成反复观看的谜影行为。
如电影《缉魂》在剧情不断地反转中,引发了观众对最后两个对望的人真正是谁的猜测。电影《神探》最后的“换枪”戏码看似将故事定格在了何家安报警自首,实则真相并非影像呈现上的那么简单,都是需要观众反复观看才能发现其中深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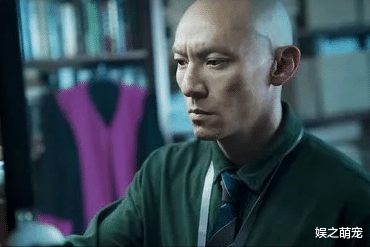
叙事要素的永久性缺失使悬念始终成了悬念,但这也是开放性结局电影的魅力所在。
二、多重聚焦:叙述视点的转换与遮蔽热内特在《叙事话语》中提出“聚焦”这一术语,将其定义为叙述者与故事中人物之间的一种“认知”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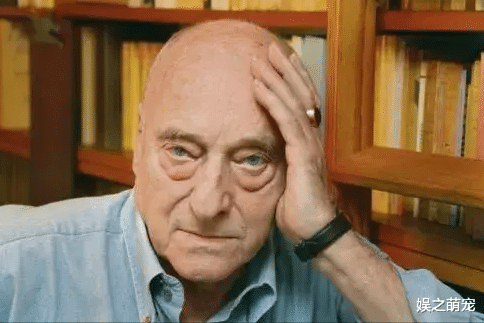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根据叙述信息受限制的程度,将聚焦分为了三种形态:首先是“零聚焦”即“叙述者>人物”;是指叙述者是全知全能的,比任何一个人知道的都要多。其次是“内聚焦”即“叙述者=人物”;是指叙述者与人物知道得一样多。
最后是“外聚焦”即“叙述者<人物”;是指叙述者比人物知道得少,观众无法得知人物的思想或情感,事件的叙述基本是局限于摄影机能拍到的画面。

而在反转叙事的电影中,常常在叙述者及视点的转换中进行排列组合,以此产生对叙事信息的不对称,通过多种视角的来回切换引发悬念的产生。
如电影《公民凯恩》试图通过不同人物对凯恩的回忆,来探寻“玫瑰花蕾”的终极含义。但从聚焦角度上而言,《公民凯恩》既是个人视角下的内聚焦,同时因对凯恩人物的不完全了解而仅凭个人判断,所以也属于外聚焦模式。
通过五人对凯恩多角度的评价使观众对凯恩是好是坏,是正义抑或是丑恶产生了好奇和兴趣,在观众对凯恩人物产生不确定时,“神秘面纱”下的玫瑰花蕾则更加“引人注目”。

电影《烈日灼心》中,对人物“陈比觉”的设置上采用了多重叙事视点的转换,影片开始交代了陈比觉因树枝扎伤眼睛而受伤,随后剧情来到七年后,观众跟随小丰叙事内聚焦的视点,得知陈比觉有智力障碍,使观众无意识地联想到陈比觉因当年事件而致伤残。
但在影片的最后,通过陈比觉得内聚焦的主观镜头陈述,揭示了陈比觉其实是在装傻的剧情反转。在此基础上,因为小丰以自身的视点出发并非真正了解陈比觉,其叙述视点由之前所谓的“外聚焦”转为事实上的“内聚焦”视点。

通过视点的转换使反转在信息差中产生,观众在接收到不对称的信息后,对事件本相产生怀疑从而促使悬念的加深,后通过“新视点”的回归,在解谜后形成反转,使观众在矛盾对立的情节中获得心灵的激荡,引发观众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和解读。
三、不可靠叙述者:人物建构上的行为偏差韦恩·布斯在其著作《小说修辞学》中提出,“当叙述者所说所作与作家的观念(也就是与隐含作家的旨意)一致的时候,我称他为可靠的叙述者,如果不一致,则称之为不可靠的叙述者。”

其中“隐含的作者”,是将创作者的个人的意识、价值观、审美趣味建构在叙事文本之上的“第二自我”,而“不可靠叙述者”是与创作者试图传达的信息、观念产生了偏差和变形,由此变得“不可靠”。
在电影中“隐含的作者”如同“大叙述者”的视角,对所发生的事全知全能,而“不可靠叙述者”是对故事的真相不了解、欺骗、隐瞒或者误解从而所产生的行动与最终结果不符的叙述,多作为故事中的“主人公”带观众进入非现实性的叙事链条,从而引发悬念的产生。

在电影中不可靠叙述者往往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首先是被动的不可靠叙述者;该类影片的叙述者,往往患有人格分裂等精神疾病或已经死亡的认知障碍,且深陷于病态的世界中而不自知,因不能正确完整地意识到自己世界的真实情况,从而作为叙述者在信息传达上产生偏差,成为一种被动的不可靠叙述者。
如电影《美丽心灵》观众跟随着约翰·纳什的视角入戏,认识了他的朋友查尔斯并了解到他为国防安全事业部工作的事情,但随着反转的到来观众才意识到约翰·纳什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上述事件都是他幻想出来的结果。

电影《致命ID》在一个破旧的汽车旅馆中,11个陌生人被迫聚集在此并接连发生命案,当真相慢慢浮出水面之后,观众才认识到11个人并非真实存在,而是交替控制麦肯·瑞夫身体的分裂人格。
其次是主动的不可靠叙述者;这类不可靠叙述者,通过运用个人超高的智商与逻辑思维能力,在对真实事件进行虚构或改编后,用诱导欺骗的方式来掩盖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刻意将观众引入错误的叙事陷阱中引发悬念的产生,成为一种主动的不可靠叙述者。

如电影《无双》观众跟随李问不可靠的视角进入故事,在和警方的一同推测下,使观众误以为国际伪钞案的主谋是警察内部吴志辉,而当真相大白之时,却发现真正的主谋李问早已逃之夭夭。
最后是先入为主或不完全知情的不可靠叙述者;这类叙述者大多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作为探寻真相的主人公出现在电影之中,又因为对信息了解得不全面,容易陷入先入为主或片面推导的尴尬境地。

如影片《全民目击》,因叙述者视角的局限性,观众跟随不同人物不断地修正着对事件真实的看法。“叙述者”是带领受众走入文本的引路人,是联系作者与人物的中介,是沟通作品与观众的桥梁,正因如此,这个引领人们入戏的“讲故事的人”就更容易取得观众的信任。
通过对叙述者性格、状态、视角等非常规化的建构,为创作者提供了制造悬念和误导观众的突破口。
热门资讯
- 悲痛!网红“涛哥”去世,死因曝光获百辆豪车送殡,赵本...
- 善恶终有报,这一次张译的话终于应验了,将“众星”底裤...
- 景甜新浪大楼亮相,圆脸大眼睛“富贵花十足”,生图也白...
- 无知还是有意为之?霍尊直播唱禁歌!
- “偶练”毕雯珺、“创1”李子璇,那些错过成团的练习生还好...
- 王俊凯,刘雨昕,王鹤棣,王子异,任泉
- 68岁张国立疑定居法国!紧抱娇妻现身高档餐厅,生活质...
- 《奔跑吧9》再次迎来家属助阵,郑恺老婆加盟,全员整蛊...
- 张雨绮:这个情路悲苦的女人,终于“解脱”了
- 王思聪又结新欢?与才17岁的姚心怡去米其林,一身穿搭...
- 曾志伟重返TVB连升三级,荣升行政委员会成员,与高层同...
- 何炅谢娜再合体乘风姐姐与好6团合跳《你好,星期六》主...
- 《法证先锋5》宣传活动买粉丝造势?TVB:不是事实
- Angelebaby翻译成中文是什么?Baby在跑男上就已给出了...
- 无视节目组规则,《极挑》后期人员这一手操作,在打导...
- 中国好声音:两轮战队赛之后,哪些学员有望成为总决赛...
- 也评电影《满江红》:解锁“九连环”般故事背后的家国情怀
- 18年后再看袁茵,才看懂她当年为何会离开侯耀文,转身...
- 王俊凯与天王同台,粉丝:这是要开启宇宙级演唱会吗?
- 又一部生猛韩片诞生,被打出9.5分,轻松夺下票房冠军!